
| 怎樣利用《和平》祈禱? |
| 《和平》首頁 |
| 本月份《和平》目錄 |
| 訂閱《和平》 |
| 二零一七年六月《和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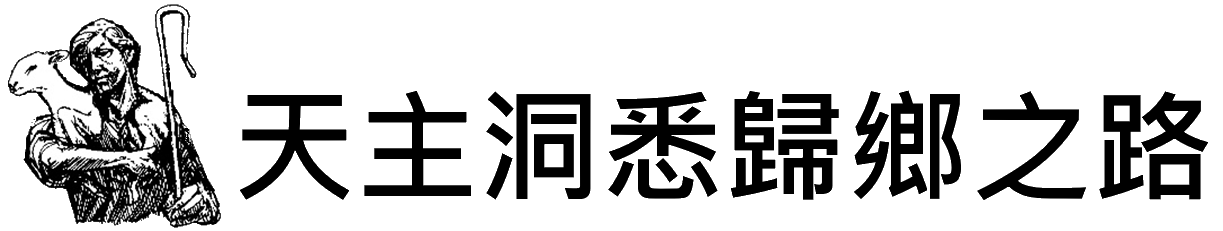 (譯自耶穌會士柏德•奧蘇利文神父 Fr Patrick O’Sullivan SJ 共七章的 God Knows How To Come Back Home) 第六章 使命和生活方式 (續前) 使命,於是,成了是對教會持「正確」態度,不可或缺的元素──渴望分擔教會的使命,會使我們真正感覺到是其中的一員。
不幸地,於此,水有時被攪濁了──在教會方面如是,在我們自己方面亦如是。教會存在,不是為她自己,而是為延續基督的使命,即建立祂聖父的王國──天主的國度。教會存在是為宏揚天國,不是為教會自己。 歷史顯示這是常存於教會內的張力,正如每一個為某個特定目的而成立的組織,都會有捨本逐末的危險,只顧自身而忽略了成立組織的目的。教會既包含人性和神聖,就不例外,所以教會這樣形容自己:「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教會恆常需要改革。 每當教會開始按自己的計劃行事,而非宏揚天主的國度,水便被攪濁,泥沙隨水飄浮,降到我們身上,模糊我們的視線,兼且通常不被我們發覺。這就是為什麼,在任何時候,教會都需要先知──那些沉浸在基督的奧秘的人,他們能夠把事情看透,提醒我們注意。 由舊約的耶肋米亞,至近代的孔格(Yves Congar)、卡爾•拉內(Karl Rahner)、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真正的先知通常都吃盡苦頭──先是遭責斥,後才得平反。澳洲的近代例子是瑪麗•麥姬洛修女(Mary McKillop)──她曾被逐出教會,現被宣為真福。依納爵本人兩次被宗教裁判所審訊並收監,後又六次受官方「調查」。獲耶穌釋放的人,不一定就是最自在的同伴。 教會經常要面對免陷於處理自己事務而忽略了使命的風險。教會所面對的,也是我們要面對的。為什麼依納爵能夠如此成功地處理這種風險,把張力化解?我提議依納爵有他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好讓我們從中得力在今天對教會持正確的態度。 第一件事我們可以學習的是友誼的價值。依納爵非常重視友誼。他和他早期的同伴們以「主內的朋友」相稱,耶穌會就是由這份友誼誕生的。 一五三八年,因為他們不能夠照原定計劃往耶路撒冷,依納爵和他的同伴便同意為教宗效勞。當教宗開始給個別成員委以前赴羅馬以外的「使命」時,他們吃了一驚,因為沒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們進退兩難──一方面他們無意拒絕教宗;另一方面他們不願意失去這份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誼。 經仔細考慮之後,他們決定成立一個新的修會,藉以保持對教宗的服膺和他們在團體中經驗到的緊密聯繫。就這樣,耶穌會誕生了──在友誼中。 這份標誌著早期同伴們的友誼質素,同樣也在日後依納爵所寫的耶穌會憲章中呈現。他筆下的憲章全是關於關係、友善的關係──與「我們的主天主」的關係,與教會的關係,與教宗的關係,與長上的關係,與團體成員之間的關係,與其他共事的人的關係,與接受我們服侍的人的關係,以及與窮人的關係。由於憲章是那麼側重以友誼為基礎,遂能培養並鼓勵一位耶穌會士「在主內」建立他所有的關係。所以,第一樣我們可以從依納爵學習的,就是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因為這使我們與教會「感受」一致,並在教會內有在家的感覺*。 在這方面,常有人說我們不需要喜歡每一個人──如果我們愛他們,便足夠了。我個人完全不同意。如果我們待人友善,便會徹底改變我們對他們的觀感。 許多年前(正如我曾經說過),當我負責培訓耶穌會修士時,團體對每天舉行感恩祭持不同意見。某主日,一位修士遲到。我發覺我在跟自己說:「他是個不錯的傢伙;我肯定他遲到的原因是合理的」,也就算了。幾分鐘後另一位修士滾進來──這人我一向感到難以對付,我發覺我在跟自己說:「他又來了;真討厭」。 兩種非常不同的反應,給我猛烈來襲,我突然明白這是因為我喜歡第一位修士,不喜歡第二位修士。這是個發人深省的反省,所以我祈求恩寵去喜歡第二位修士。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這故事有一個美好的結局──到他決定離開修會時,我們已經成為好友。友善的態度,這是人人都可以祈求的恩寵,也是為拓展天國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的恩寵──這引領我們到第二點。 依納爵有強烈的使命感──他最深的願望是被安置與耶穌在一起,以祂的十字架為準繩,分擔祂的使命。我們從他的自傳中,看到他的祈禱獲得俯允:「他[依納爵]決定在晉鐸之後的一年內,都不主持彌撒,為準備自己並為祈求聖母屈尊俯就把他安置與她的聖子在一起。一天,當距離羅馬尚餘數英里的路程,他在一間聖堂裏祈禱,並經歷到靈魂的奇妙變化,他毫無疑問地清楚看到天父把他安置與祂的聖子基督在一起…」(自傳96號)。
這裏必須強調,依納爵的使命感,生於降服──一種深切愛慕委順於基督的奧秘的態度,如上述引文清楚表明的。由此,愈降服於基督的奧秘,我們愈會感覺到被吸引成為在世上延續祂使命的教會成員之一。 也許,一個不易被接受的實用方法:要量度我們對基督奧秘的降服程度,可看我們與教會內其他成員保持友好關係的程度。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一些人熱愛真理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有敵人。又或正如查理斯•謝爾敦(Charles Shelton)所說的:「當我們相信真理派用場,我們很容易會『放棄』其他如包容、審慎和明晰的美德」。 結束這一節:對教會的歸屬感加強我們對天主眷顧我們的意識。依納爵的兩個洞見可以幫助我們產生歸屬感:友好關係的重要性;降服於基督的奧秘,會使我們切願在教會內分擔祂的使命。 貧窮及對窮人的愛
於是,這裏有兩個純粹從政治或經濟體系的觀點,都是互不相容的要求;可是感恩祭將兩者相連,並嘗試將兩者在人的心底結合:偕同天主的貧窮而貧窮,這是天國的基本價值,藉以對抗沒價值的貧窮,為伸張正義而必須消滅的貧窮。 ──── 第六章完 ────
© Copyright Shalom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