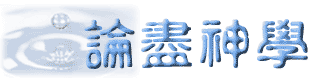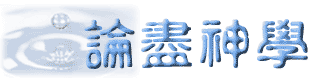|
Ignatius
|
Posted -
2006/8/10 下午 01:47:57
|
|
|
司鐸靈修
甘易逢著
陳寬薇譯
過去十年,我們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內,都可以看到靈修的再發現。歷代以來,幾乎都是只從工作和行動上看使徒事業。在這樣的觀點之下,自然會强調司鐸的聖統性和服務性。但是漸漸的,我們必須承認既非工作,也不是機構組織或靈牧論文,能够培養真正的基督徒。堂區神父能够通傳給信友的,只是那些在靈修生活所培養的,也就是說為靈性活力所推動,從他們自己基督徒生活的深處所放射出來的東西。
大家的興趣似乎也漸漸脫離推理性的神學,而向靈修集中。因此,我們看到對基督徒生活之內涵的再認識,愈來愈不以行動或一種思想來界定它,而更趨向集合兩者的「靈修」。
只有一個天主、一個主、一個神,但是靈修卻有很多種,全都是聖神在基督徒內的特有行動。有先知神恩、使徒、導師以及許多其他神恩。每一種神恩,都是天主的贈予,各有它相對的靈修;每種靈修,一方面以相對的神恩為依據;另一方面則以所活動的環境為依據。
所以,每一種靈修都栽植在基督徒生活的靈性活力中,同時又為文化所浸染。這裏所說的文化,主要是指它深厚的根基。我們並不需要長篇引述,以堅持生長在佛學環境中的司鐸,與出自儒家環境的司鐸,一定具有不同的靈修。靈修中的毫釐差異,它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們僅在此解答一般性司鐸靈修中的難題,但着眼點是在東亞。大膽觸及這樣一個主題,難免有夢想之嫌,不過這樣的遐思也能開拓新眼界。
教會內的司鐸靈修
我們每一位司鐸,在教會內都有自己的地位;雖說全體信友都是「祭司」,但是平信友的祭司身分與神父們畢竟不同。任何一位,如果要將兩者簡化為同一種靈修,到後來他自己就分不清自己是誰了「祭司」是指在教會內,領受一項特別職權的人。當然,我們這裏是針對神父所說的,用在主教身上更為恰當,他們所領受的是完整的祭司品位。這份職權是聖事性和牧靈性的服務,包含教化信友,引導他們經由聖事,共享基督生命的真蘊。這是基督徒奧蹟的真像,忽略了它也就不再是基督的門徒了。基督願意藉着特選的人,以特有的方式繼續祂的中介任務。
基督徒的祭司,其要點是取自基督的祭司形像,不是其他宗教的祭司形像。基督徒祭司,不應取法道教中的道士形像。或佛教中的法師形像。但無論如何,在具體文化中,祭司的靈修,不可能不受當代文化大師們的影響,而這些大師們又受了先賢們代代相傳的影響。所以,基督徒的祭司是既附着教會內,又與人類社會的各不同文化和宗教相繫的。
雖然說神父與平信友的司身分不同,但是我們不能將它們分離,更不可將兩者對立。Paul Evdokimov說得好:「每一項職務,每一層聖統性品位,都是在教會之內作用,總不可能在它之上或超過它而作用之,因為每一職務牽引出其他職務,彼此相互共存。祝聖的祭司與平信友祭司,兩者相對立,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全體基督徒是同一身體的肢體。主教團確保宗徒使命的繼續流傳,以便將人們變成信友、兄弟姊妹,進而使天主的子民成為祭司的王國、皇家的祭司……」(註1)。
所以祭司的靈修必須包括這樣的基本透視,即「實際上世界尚未隷屬基督,而平信友的祭司身分就因此發生作用。平信友的地位是既在教會內,又在世界中」(註2)。那麽,神父的祭司身分,經由平信友的祭司身分而得以完成。一位神父的靈修,必須帶有這基本的特徵,而讓自己回到人類環境中。他不可以毫不考慮自己與平信友的關係,以及他們與世界和人類狀況的關係,而擅取立法的權力。
危險在於所有的職務都趨於自行獨立,與平信友分開。因此,我們務必經常注意祭司職務,與教會整體以及天主子民之間的關係。
梵二「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中指出,司鐸的首要職務,是服務聖道,但還有兩項是同等重要的,即他的聖事性和靈牧性的角色。這樣,司鐸職務是三等分的,司鐸靈修也就從這三項職務中吐出芬芳,而賦與這靈修生氣和活力的神,必須是基督之神。基督本人既是最完美的「言」,也是此言的服務者;祂既由父愛所生,又成為這愛的聖事,尤其是在聖體內;他既是永恆的牧者,又在我們中作了為羣羊犠牲性命的善牧。我們若置身基督的心態與自我意識中,便是回到了司鐸靈修的泉源。
司鐸與文化
聖保祿比任何人都清楚宣講聖言的緊急性,在他來說,「傳福音,原沒什麽可誇耀的……我是奉命去傳,我若不傳福音就有禍了」﹙格前九16﹚他給羅馬人所寫的信上說:「信仰是從聽信息而來的,而聽信息是從傳揚基督而來」﹙羅十19﹚。喚醒信仰,宣講是必須的。凡呼喊主的聖名的,必定得救,「但是,他們沒有信祂,怎能呼求祂呢?沒有聽信息,又怎能信祂呢?信息未經傳報,怎能聽見呢?」﹙羅十14﹚。
這是宣講聖言之緊急性的根本所在。子是天主之言,這「言」是非說出來不可的,而說這言時,是對具體的人說的,而他們各有其固有文化。因此,聖言的服務者,必須懂得在他傳播聖言的具體文化中所用的教授法,全球的學校是非常相同的。這句話在傳授科學方面也許可以講得過去﹙但也不是不證自明﹚。但是,信仰的輸送,是必須觸及人們日常生活,甚至深入心靈底層,那麽,教授的方法,在中國和非洲就不可相同了。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國幾千年來的教育經驗,以及對先賢遺教的反覆背誦;而在非洲那邊,我相信必須用另一種傳授和啟發的方法,來配合他們古老的傳統。雖說孔子已被中共排斥,但是長遠的教化已使儒教在中國蓋上了永久的標記,就連毛澤東主義,雖然反對這位先師,還是踏在他的腳印上,只是腳步過重了一點罷了。中庸首章的話,可以概括儒教傳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
當然,在教會所接觸的各國各地,創造全新的司鐸靈修,以配合不同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必須體會到:歷代所出現的司鐸形像,都是由地方上的習慣和傳統中產生的,因為基督並沒有留下司鐸的「模型」。
所以,我們勢必按照文化與宗教,談論不同形態的司鐸靈修。那麽,也就需要認清,基督之紀元出現時,他以新宗教的大祭司姿態出現,所造成的改變,甚至革命。這位大祭司和猶太社會的祭司截然不同。
希伯來書信是最符合我們的主題的新約作品。這書信的作者,使我們知道從猶太的祭司觀,到基督徒司觀之間,在神學、靈修禮儀上的進展。該書信所强調的一點頗值得注意:「如果說基督的死亡、使祂享有大祭司的光榮,那因為這死對天主是孝順地服從,以兄弟之情與人類結合」(註3)。
成為一位祭司,基督必須「在各方面和弟兄們相同」,這就是書信中明的:「祂必須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們相同,在天主面前作仁慈而可靠的祭司,使人的罪得到赦免。由於祂親自經驗過考驗。受折磨的痛苦,祂現在才能够幫助那些受考驗的人」﹙希二17~18﹚(註4)。
每一位神父也必須這樣,不論身處何方,他的地方化應使他在各方面都和「弟兄們相同」,這一點要求他的靈修基礎、深植耶穌聖心和當地文化的內層。基督在各方面和弟兄們相同,所以,每位神父也要變成和周遭的人相同。這才是一位「中介者」。這種相同不是外在的一致,而是內心的同化,像基督那樣;除了罪以外,祂全都和我們一樣。這一點應是司鐸靈修的基要點。
司鐸的形像
基督的祭司身分,既不能用猶太宗教的規範表示,同樣也不能和其他宗教的祭司,或賢哲大師等同化。人類的任何一種智慧,都走向新啟示的基地,這話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不論人們所崇拜的大師有多麽了不起,他們的智慧須都從啟示的觀點加以衡量,任何啟示是隨着對基督的接受和認識,漸趨寬廣而明朗的。基督固然聲稱不是來廢除法律,而是來完成,但祂不斷的堅持,祂帶來的信息包含兩方面,一是進行、一是終了。這也就是本地化的命運。基督帶來持續與終了。
基督徒信息之所以新穎,在於基督本人,而不只是祂的話。如今,這信息必須在每一文化中喚起它潛在內涵的湧現,使它們綻放基督徒的活力。所以,基督徒生活的本地化,是一種適應和插入,另方面又是蛻變與催化。因此,一位司鐸,聖言的服務者必須認清,這「聖言」是天主,而不是人,沒有一種文化能够提供一個符合基督要求的完美祭司模式。猶太宗教也同樣不能,雖然他們是特選的。
至聖先師孔子―—每位司鐸實都應該是位大師―—本人一定承認這點,他之所以不談神明的奧秘,就是因為他不知道要怎樣說。反過來說,如果基督談論了,那是因為他自信知道這些事,而且能設法介紹它們。為了使問題的重點更為清楚起見,我們可以說實在需要受靈感推動的先知們,寫出「致中國人書信」、「致印度人書信」、「致日本人書信」,幫助他們把握新祭司的涵義,進而明瞭各自不同的靈修形態。
根據福音的記載,基督根本從未以自己為「祭司」﹙按我們今日所了解的意義﹚,也沒有按猶太的形態以自己為「祭司」。在同時代的人心目中,尤其是在猶太宗教中有地位者的眼中,祂只是一個俗人,卻僭取篡奪來的權力。所以,法利塞人才要祂提出證據,表明祂是天主所派遣的。按猶太傳統,祭司是與眾分離的,鶴立雞羣對神禮拜的。基督也是與眾不同的,但是卻不與人類分離,祂深知他們的苦楚。
司鐸行使職務時的危險,是與信友保持一般距離,而以大祭司自居,就像一位士大夫。對所有擁有權勢的神父,在所有人類社會中都有相似的危險在等待着他們。到了這裏,再走向一律規則化,一切由個人決定,就只剩下很小的一步了。任何一種本地化都在冒險,就是因為接受一種文化的優長時,也吸收了它所短缺的一面。
在階級分明制度及階級嚴謹的社會裏,神父絕對不會找不到極易模仿的形像。家族社會中的「父親」形像,也能成為司鐸的「父性」模式,但這並不完全符合基督的教誨。在一個社會中,父親的形像若是相當嚴肅而陌生的,那麽,生活其中的神父,在未以司鐸靈修的其他因素修正它之前,就套用這模式是不適宜的。東方的傳統裏,有多種類形的祭司和修道者。我不會勸人模仿巫師,輸送神力扮演治療者的角色,這等於歪曲了基督留在教會內的聖事性功能。一位神父清楚知道,自己在這方面領受了一些特殊能力,而這能力與巫師、魔師的法力不同,這樣的認識是很適宜的。今日教會內,很多信友和神父,都夢想擁有特殊能力,似乎那就是既主要且正確的聖神標記,我們切莫忘記,七十二位門徒傳教歸來時耶穌的反應;祂靜靜的聽,我相信有些門徒一定頗為囂張得意。耶穌聽完後略帶幽默的說:「我看見撒殫如閃電般從天跌下」,然後又說:「我已經授給你們權柄,使你們踐踏在蛇蠍上,並能制伏仇敵的一切勢力,沒有什麼能傷害你們。但是,不要因為魔鬼屈服於你們而高興,你們應該高興的,是你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天上了」﹙路十18~20﹚。
在所有的宗教、文化和各家師門中,多少都能找到像耶穌那樣的祭司形像, 但是這些形像都必須加以改變和超越。我們在真正的印度教、佛教和其他宗教地區,可以看到令人尊重的祭司或修道者。利瑪竇曾以西方學者的姿態自居,那是因為他要盡力呈現基督宗教中的祭司形像;後來便不穿僧服,不作洋和尚狀了,那是因為他最後認清的這形像,也就是他身邊人早就有的形像,並不能作為他要傳遞的基督徒祭司的支柱。在印度,De Nobili神父將自己變成當地的托鉢僧;我們也聽說過一些隱修神父,按照當地穩修者的方式生活。這種種神父形態都能有利的取代士大夫神父、大老闆或總經理形的神父形態。這一方面的本地化工作,我們仍有很長的一般路要走,不過,全球各國都在做這方面的嘗試。例如工人神父,確實為司鐸靈修開啟新的路徑,其他有勇氣作開路先鋒的神父們,也同樣功不可沒。
一種「東方」靈修
如果全球各地的司鐸靈修,都能以同一方式表達,那麽,我們談起來就實際多了;而羅馬也就可以遙控自如了。但當我們進入梵二精神時,這簡真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不要忘了,教會正邁入它歷史的第三時代;就像拉內﹙Karl Rahner﹚神父所說的:「從神學上說,教會的歷史有三大時代。第三時代剛開始,並在梵二大公會議中正式展現。第一時代是短暫的猶太基督徒時期;第二時代是教會走進另一不同的文化地區,即希臘與歐洲的文化與文明;第三時代教會的生活環境,實際上是全球。這三個時期指出三項主要而不同的基督精神及宣講此精神的基本情勢」(註5)。
以拉內神父的看法,保祿向外邦人的宣講,「在教會歷史中,開創了一個新時期,他不是將猶太的基督徒生活外銷給僑居外郷的猶太人,而是與歷史性的耶穌相連,並在外郷上土地上生長的基督徒生活。我知道我說的話模糊不清,但我認為困難也就正出在由猶太基督徒生活,轉變為外邦人的基督徒生活,這中間牽涉到神學問題,這些問題絕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麽簡單……」﹙Ibid p. 721﹚。
我們可以這麽說:梵二大公會議以後教會已正正式進入它歷史的第三時期,它已是足跡遍佈全球。正像拉內神父所說的:「梵二大公會議,正在摸索尋求認同,尋求普世性教會的第一個正式的自我實現」﹙Ibid p. 717﹚。按照拉內神父的意思,教會演變為「普世性」的新經驗,將為它帶來一些後果。它們和猶太基督徒教會,在轉為外邦人的教會時的情形類似。唯有歷史能說明,教會擴充至普世性範疇,對基督徒的神學和靈修究竟有何意義。我們知道會有大的改變,但卻說不出將是怎麽個樣子。
在這曙光初露的新時期,我們先來看看基督徒生活的核心發展,真正的神學反省隨後跟進。因此,我們先看所興起的,與西方進口的傳統靈修相異的靈修形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亞洲主教們在加爾各答開會,必「祈禱」作為大會主題。他們會議的最後宣言,為普世教會是一項重要文件。它宣佈了教會官方已覺察到,在亞洲教會中,一般基督思想及司鐸靈修在漫長本位化的過程中,已進入一個新階段。
文件中列舉原則,至於實際果實則需由每個基督徒團體,和每位神父自己去摘取。在Briefer Version of The Final Statement的第八節「本位化」中,我們看到:「我們各地方教會的祈禱生活,應該吸收各民族的富藏;這些富藏是給于基督作為產業的。其中特別是我們大師所發揚的某些祈禱方式,在形成我們文化傳統中,扮演了重要而令人起敬的角色。聖神正領導着亞洲教會,將我們傳統的祈禱和敬禮中最精華的部分與基督徒的寶藏匯合為一」(註6)。
到達這樣的匯合,需要長久時間,所有信友都必須認清自己的角色。首先,這不是神學家的工作,而是整個教會的工作。但是,在這些地方教會中,主教和神父肩負最重的職責,因為由於特殊的原因,他們是基督的執行人。他們必須比其他的人更是祈禱之人。亞洲主教們在加爾各答所作的宣言,最主要是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神父說的。
文件中指出:「亞洲對正確的基督徒靈修,能有很大的貢獻:已有豐富發展的身、魂靈合一的祈禱;潛入內心的祈禱;克己苦行的傳統;古老的東方宗教所擁有的觀照之道;其他簡樸的禱告,以及一般百姓信仰和虔誠的表達,這些人的心靈平日就是傾向天主的。這是亞洲獻給教會的祈禱禮物」﹙ibld.﹚。
首先出現的問題就是地方性的傳統。事情並不在於塑造自己,使和舊傳統相符,使它們重獲活力。當然,這是對本位化和尋根的最糟的懂法。因為所有的本位化和文化復興運動都應有的特徵是,一面新發現傳統的精神所在,另一方面不斷適應目前情況。
如果以道家、釋家或儒家的模式來重塑基督徒司鐸的形像,簡真是荒謬。其實,基督徒司鐸的形像,應經多世紀文化的影響,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一位來自亞洲的基督徒司鐸,實在不需要維持從西方進口的生活形態。他必須藉每一文化中已有代表上主之人的形像作適度的適應。
一項基本的靈修
司鐸是從信友中選出來,代表他們奉獻禱告與犠牲的。我們都知道有哪些陷阱在等着那些從百姓中選出,享有特殊權力和知識的人。他們很容易忘記自己是從隊伍中升上來的;反而假借蒙召管理天主的教會之名,變成獨裁者。靈性方面的權力,同樣可以變成現世各權力的根源,一加行使便破壞了主耶穌所留下的理想司鐸。仗持着文化,一位神父可以自炫為大法師、士大夫或精神領袖,以濫用信友的輕易信任,來堆集自己的財富。
我們都有妄用司鐸職權的危險。所以,我們必項回到最基礎的靈修,這樣,不論在那裏,都能從內心湧現一個基督的祭司的生活。
如果司鐸必須教信友們祈禱,那麽,他自己的祈禱就不應該是離羣的,而是真真實實與信友的祈禱合為一體的。這樣的祈禱,它的靈感和力量,來自司鐸與信友團體日常相處的關係。保祿就是這樣教他的信友們祈禱,即是在基督內,藉着基督、將自己的生活和天主的生活相合。保祿的整個靈修經驗,在每個信友生活的具體環境中,作不斷的再認識。他沒有編寫一本祈禱手冊;但他為他們示範,如何在實際狀況中與天主建立關係,藉此而教給了他們祈禱的要訣。在以上所引述文章中,拉內神父說明教會從保祿開始,走出了猶太基督徒的世界,而這是非比尋常的一大步。假使保祿一直在猶太基督徒環境裏生活,一定會另有一種司鐸方式。如今教會已進入普世層面,同樣問題也再次興起。當然,我們並不是意謂着「切斷」,但往前跨一步是必要的,東亞和非洲都要各按其環境邁步。
如果神父們明瞭目前正在成形的新現像,便會對含苞待放的司鐸修開放,聖神也正透過多種文化在邀請他們。這種靈修將是水乳交融般,含有各民族,各文化的精萃,那都是梵二邀請我們去欣賞喜愛的。如果在這方面,我們追隨保祿的足跡,必將越來越相似主耶穌:祂本是天主聖言,卻跑來看看如何能以人的生活,將祂和父的關係活龍活現的顯示出來。希伯來書中告訴我們:「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五8﹚。這就是一位神父,一位懂得體認痛苦、焦慮、悽慘的人,如果他真要肖似基督,必須經驗這一切。正如所引述的希伯來書信中的話,基督必須使自己在各方面都和人相似,才能做他們的大祭司。「祂必須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相似,才能成為天人之間,仁慈而可信任的大祭司,洗去人們的罪汚」(註7)。
重要的倒不是說神父應該成為專業祈禱的佼佼者―—如果我可以這麽說—―,因為任何人,多下點工夫都可能做到這點的。但是,他必須在每日生活中,再去發掘基督對天父、對人類的深入態度。這樣,神父不會只是一位被請去為亡者獻祭,為新人祝福的祭司,而將是周遭人,在天人和人人關係中的楷模。如此一來,神父才真能幫助信友,在日常生活中重獲天人意識——不是抽象的生活,而是在具體國家與文化中的生活,如果一位神父認清了這理想,他就變成了聖神的中介,幫助信友去解釋一切生活中的遭遇。他藉着交付給他的父性能力呈現了天父,藉着啟示子的話呈現了子;他藉聖神的恩寵變成一個為人們的痛苦和喜樂帶來意義的人。因此,司鐸的基本靈修,在人類的每一偉大傳統中,都有它特別的芬芳。任何人只要對東方教會的聖職人員有少許的認識,便可知道司鐸靈修可以在每個文化環境中別具韻味了。
司鐸、天國的記與證明
司鐸應該是一位對無形現實極度敏銳的人。問題就在於我們已經將那些現實,「澄清」得失去了它們的神聖特徵。在很多人看來,司鐸只是一種職務,其實它是一件奧蹟,是一件聖事。所以,不僅晋鐸典禮是一件聖事,一位司鐸的一生必須成為一件聖事。一位司鐸應該是人與神之關係上的一件聖事,這一層應貫穿他整個人和全部生活。希伯來書信中將一些話放進基督口裏,說給天父聽,就是在告訴我們這一點:「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要,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十5﹚。基督不是到世界上來奉獻犠牲和祭品,而是在人的生涯中,將自己作為一個完全給與天主和弟兄們的人。身司鐸的基督與人們的關係,由Vanhoye神父的一句話完全表達出來了:「基督在同一和唯一的事跡裏,完全實踐了祂與人的結合,降到他們的痛苦深淵中;另一方面,以祂的哀求和委順,已將天主的超凡行動帶進那深淵,因此,在祂內創造了一個新人,完全與天父相合,並有益於鄰人」(註8 )。
問題在於很多人,認為天國是現世的東西,它能够像人類社會這樣組織起來的。的確,我們可以,甚至應該讓教會有它的架構,因為它是人所組成的!不過,在人類社會,權力總想嶄露頭角的。其實,天主的國在於天主統轄人心,就像祂曾統轄基督的心那樣。這天國只有在基督身上完全實現了。祂對親近祂的人不斷重複的說:「你離天國很近了」,或者「天主的國近了」。在祂的母親瑪利亞身上,藉着獨一的恩寵,天國實現了,她的確和她的兒子一起進入天國。
至於我們,則是朝着那美妙之境前進。而司鐸應該是天國臨近,和它的實現的證人。天國已從各方臨近了!它從大地的每一角落升起,它比教會向世界展開之始來得更真實……或者更應說它比天國在星空之下誕生時更為真實。
我倒希望看到日後的司鐸形像能百花齊放。目前只如晨曦初現,含苞待放呢!萬物有靈論﹙animism﹚的信仰者常强烈地表現了他們對奧秘的深刻意義。為何不能盼望司鐸按自己的信仰把對奧秘的意識靈性化而傳衍至後代呢?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退回到某些文化中仍舊保存着的萬物有靈論,但是,我們必須取用中神聖的一面,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就是我們這些負有喚醒他人對神明意識之責的人所缺少的;我指的是覺察受造界之神聖性的能力。我們知道偉大的基督徒神秘學家,他們有這股深沉的神聖與奧秘感,也懂得日益使之加深,可是,人們卻視他們為離羣的生命體……
如果司鐸辨明了自己的角色,是人與創造者之間一切關係的啟示者和開創者,那麽,實踐梵二「司鐸生活與職務法令」中的期望就容易多了!它所描述的司鐸就是天主在世間的明證。
問題並不在於變成苦行者,或是某種宗教中的司禮者,但是,我們必須盡一生的努力去追尋天主,為自己的宗教,貢獻出其他大師為他們的宗教所貢獻的種種。這樣,我就會發現有多少種不同作神父的方式。有人顯示天主的父性,有人只是簡單地與兄弟姊妹相處,讓人體會天主在他們之中;這兩者的﹙靈修﹚是有很大的差異的。我們不要忘記,基督與祂當代的人很親近地生活在一起。祂從來沒有像經師和法利塞人那樣,與百姓保持距離。基督留下的「模式」不能重現,這「模式」是來自內在的基本原型,必須以不同的形態表彰它。因此,讓基督之神繼續不斷在教會內作用吧!羅馬式的神父形像絕不是做神父的唯一方式,還有別的許許多多的方式。在此回想一下Paul Evdo kimov的原則,可能是有用的:「基督的神聖職務,藉着平信友在歷史中進行,它是一項『積極的末世』職務,準備世界迎接末日」(註9)。這話幫助我們從整個救援計劃及它和民族文化的關係中,看司鐸靈修,因為畢竟是信友團體比神父更浸潤於文化和日常習俗中。
傳統與進步
一談到本位化這類問題,很多人便會反對,因為他們似乎看到考古學中的幽靈出現。其實,回到根源上,並不是要和過去的一致,而是讓那給古老文化活力的動力,來到我們身上。當然,在這樣的流轉中,總會為我們帶來一些古董,但那並不是重要的。
所以,傳統文化中沒有一種祭司形像能完全滿足基督徒祭司的形像。這形像是和基督本人相貼合的,由於祂是一位祭司,而沒有祭司的形像。他們按照默基瑟德—―他無父又無母——的品位,稱基督為祭司,是要讓我們明白,祂不屬於猶太教宗的祭司行列,祂永為祭司。正是基督這種超文化,超現世的祭司特徵,可以隨時代與文化之不同而形成千萬種形態。司鐸的身分越被定型在固定模式裏,他越應警覺到它的相對性,它不可能永遠是一樣的,它勢必轉向另一種形式。可是,神父們常會有相反的反應,即設法將某種相對性,使其絕對化。
一位神父可以選擇修練放棄現世一切事物的美德,做一個靈性世界的證人;他可以被尊為祈禱的人,承受了天主賜予的深奧智慧;他也可以被視為像儒家、佛家、道家傳統中的智者。
任何宗教的信友,對天人之間的中介者所擁有的能力,是很敏感的,我們不可以排斥祭司身分中的這一面。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信友們都指望他們的牧人享有某些聖事性的能力……一位司鐸為什麼不能做當地的聖人呢?唯一的難題是選擇作什麼樣子的聖人。
我知道,這樣的本地化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但適應目前的文化,這是無論如何要做的事,那麽為什麼不作刻意的努力,在「羊羣的模範」﹙伯前五3﹚的思想下,將基督徒司鐸的實際情形真正本位化呢?我們的羊羣是完全浸潤在今日的世界和文化裏,神父必須成為信友的內在模範。所有的信友,和組合這個社會的其他人士一樣,度的完全是人類社會的生活。
做司鐸的勇氣
一位神父認清他應該是怎麽樣的人後,需要勇氣去實踐,躱避自己的司鐸身分,有兩條路子:一是自抬身價,高居信友之上,遠離人類團體;二是拒絕「與眾不同」一心只要和其他人完全一樣。他假藉大家在一起之名,讓自己像其他人一樣。這樣一來,他有一種不是高居別人之上的滿足感。可是,如果一個人忽略了他之所以和別人一樣的目的,是要喚醒別人,辨認那超超我們卻又實在深植生活中的現實,那麽,他又不是他所應是的樣子了。
當然,一定有一種適合於神父的作人之道,就是基督所示範之道,朋友與朋友相處之道。當所有的特權都被奪去,神父和每個人一樣,就只是個人,像中國大陸上幾百名神父那樣時,神父還有什麼呢?無!真的無;但也是全有!他擁有驚人的能力,使他隨即明白善良、誠實、自由的具體化,讓他變成「為所有人」的人,無限量的了解他人,但卻無能妥協或阿諛奉承。
如果一位神父認清他所接受的祝聖,自會懂得這個祝聖不是使他離羣,而是使他像基督一樣,做一個完人,當然,他將常是一個罪人,但假如他從人性的角度,而不從尊嚴、權力的角度、看自己司鐸的身分,便比較容易被視為另一位基督。我所說的話,早已有很多人說過了,在此重複,同時將這一點,作為司鐸靈修的核心,或許還是有用的。
我情不自禁又要回到希伯來書信,它在基督身上給司鐸下定義:「我們所有的,不是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祭司,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受考驗的,只是沒有罪過」﹙四15﹚。在人類的各種情況中,司鐸都應該是一位安慰者和中介人。這樣,為他來說,作聖事的分施者,或祈禱的管理者就不是首要的了。他本人勢必成為整個基督徒人生的聖事,就像基督曾經做過的,如今仍舊不變。
如果司鐸身分真是人所生活的一種現實,而不僅是一項職務,那麽,必須要有司鐸靈修……司鐸靈修之所以真實,就是因為司鐸身分實地觸及人生全部現實直到存有的最深處。這樣的態度看司鐸身分,會使某些人可能感到奇怪……其實,這個觀點破碎了純職務性的司鐸觀,而視之為一種生活和存有的方式,和基督所做的一樣。這個理想,凝聚在人性的最深層,而在帶有地方文化色彩的靈修中表露。這理想是單純的:肖似基督;像保祿所做的一樣,經由祂並藉着祂而生活。
為了將司鐸靈修置於照亮我們的途徑的末世觀念中,要回想一下 Paul Evdo kimov的話,是有利的:「在末世,最終極的基督徒職務,基督徒的希望,有賴於信友的祭司身分」(註10)基督的「終結」是世界的得救,也就是說,全人類在基督之光和基督的恩寵中,走向真實的人生。當我們這樣思想時,上述引言就變得清楚了。
註:
1.Paul Evodokimov, La femme et le salut du monde, Desclée de Brouwer, 1978. p.104
2.Ibid. p. 105.
3.Albert Vanhoye,Prêtres anciens. Prêtre nouveau, le Nouveau Testament, Paris, Ed. du Seuil, p. 100.
4.Ibid. p. 87.
5.Karl Rahner, “Notes towards a Fundamental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Vatican II, ” in Theological Studies, 40 (1979) 721.
6.EABC Papers. No. 13, Prayer-The Life of the Church of Asia, p. 35.
7.A. Vanhoye, op. cit., p. 104.
8.Ibid. p. 160.
9.P. Evdokimov, op. cit., p. 106.
10.ibid. p. 113.
本文譯自:Yves Raguin, S. J., “Priestly Spirituality,” East Asia Pastoral Review, XVIII(1981) 8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