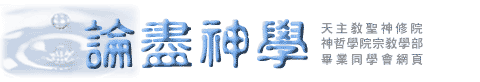
蔡惠民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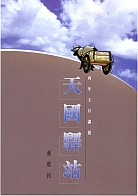
|
|
天國驛站
蔡惠民神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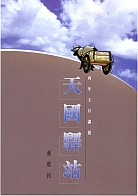 |
|
多默的懷疑 有一次,一個主日學導師給小朋友講解耶穌的復活。為了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她首先邀請小朋友猜一個謎。「甚麼是身上長滿毛,頭上有一對長耳朵的?」全場靜默,沒有小朋友舉手作答。導師繼續問:「甚麼是口裡長了大門牙,日常喜歡吃胡蘿蔔的?」依然沒有反應。導師覺得有點奇怪,進一步提示說:「它雖然比烏龜跑得快,但由於驕傲,曾經跑輸給烏龜的。你們猜是甚麼呢?」一個小朋友終於按捺不住舉手說:「姐姐,我知道你希望的答案是耶穌,但我覺得它應該是兔子!」 |
丙年主日講道 復活期第二主日 |
很多人誤以為信仰是一套不容挑戰或懷疑的教義,如果有所懷疑,也只能藏之於心,不敢宣之於口,否則便是離經背道。故事裡的小朋友從主日學開始便被灌輸這種看法,他以為無論導師問甚麼問題,希望聽到的答案都是耶穌,以致他認為答案應該是兔子,也不敢提出。最後,幾經掙扎,才有勇氣說出來。
當復活的基督向門徒顯現時,多默不在場。如果其他門徒因害怕猶太人而把自己關在屋裡,多默的不在場,是否暗示他比其他門徒更大膽,更有勇氣面對困難和挑戰?後來其他門徒對他說:「我們看見了主。」基於多年的日夕相處,多默未必懷疑其他門徒的誠信,不過,理智上他實在無法認同。耶穌明明已經死在十字架上,並被包裹安葬在墳墓裡,這是他親眼目擊的。人死又怎能復生呢?無論其他門徒的見證如何言之鑿鑿,多默也無法說服自己的理智去接受。
置身多默的處境,你會感到壓力嗎?如果堅持自己的看法,其他人會怎樣看自己?「老是唱反調」,「信德薄弱」,「不服從權威」等帽子便接踵而來。反過來,如果掩著良心,人云亦云,做個「二手」基督徒又有甚麼意思?假若教會團體內也沒有自由表達意見,或提出質疑的空間,那麼,教會跟那些歌功頌德,訶諛奉承的團體又有甚麼分別?由此可見,多默的懷疑是誠懇的。在那一刻,縱使其他門徒給他不少壓力,多默始終堅持信仰必須來自身體力行,真知灼見:「我除非見他身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若20:25)
幸虧初期教會有多默這類門徒。雖然未能完全認同團體的信仰,他沒有離開,一刀兩斷;也沒有陽奉陰違,表面接受團體的看法,內裡卻被動抗拒。反之,他繼續留在團體中,真誠開放,在多方的壓力下,堅持對話,尋求理解。多默的勇氣和挑戰,不單沒有損害教會的信仰,反使教會的信仰更成熟,更有說服力。如果教會團體每次信仰上遇到懷疑和挑戰,只會訴諸權威而沒有實事求是面對問題,信仰最終只會淪為陳腔濫調,失去應有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一如當年的門徒團體,今天教會亦需要多默這類門徒。在一個經常受到恐怖主義威脅和襲擊的地方,教會應繼續支持依拉克戰爭抑或撤軍?在一個信仰不完全自由的國家,教會應堅守原則,努力抗爭,抑或靈活變通,善用一切可行空間?面對政府的不合理施政,教會是猜疑對立,寸步不讓,抑或互諒互讓,尋求共識?縱使大多數人已有既定的立場,或者權威已作了最後的決定,另類的聲音和異見的空間也不能封殺。
在香港,教會團體在「居港權」,「人大釋法」,「校本管理」等問題上也意見分殊,一方面領導已有清楚的立場,另一方面內部亦有不同的聲音。教會應怎樣面對這些信仰上的懷疑和挑戰?是否聚在一起,把門關上便可解決問題?或許多默當年的壓力又再浮現,但我們無須為此而感到不安,也無須勉強自己附和一個不認同的立場。與教會團體或教會權威的觀點不同,並不代表自己再不是團體一份子,反之,我們應留在團體中,因為團體才是我們弄清問題的地方。當年多默也是在團體中經驗到復活的基督,在團體耐性的接納下,內心的問題和疑慮最終得到化解。
因此,復活的見證不是不容挑戰和懷疑的教義。復活的見證是來自團體中不同意見的真誠開放。幾時人與人之間能坦誠相向,彼此尊重,我們便會相互受益,發現一個不容易看見的生命,即復活的生命。教會負起托管和傳遞信仰的使命,是要讓人在團體中,放下焦慮,疑惑和心理障礙,向新的可能,新的視野,新的體會開放。復活的生命就是理想得到實現,過錯得到寬恕,困難得到解決,創傷得到治療,病弱得到照顧,饑餓得到飽餐,靈性得到滋潤,罪惡得到克勝。多默便是在一個充滿接納和愛的團體中,發現復活的基督。
主已復活,是我們再次從疑惑到信仰,從恐懼到喜樂,從死亡到生命的宣告。沒有多默坦誠的懷疑和衝擊,復活基督在教會的顯現不會明顯,也不會教人由衷地相信:「我主,我的天主!」(若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