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怎樣利用《和平》祈禱? |
| 《和平》首頁 |
| 本月份《和平》目錄 |
| 訂閱《和平》 |
| 二零一四年 八月《和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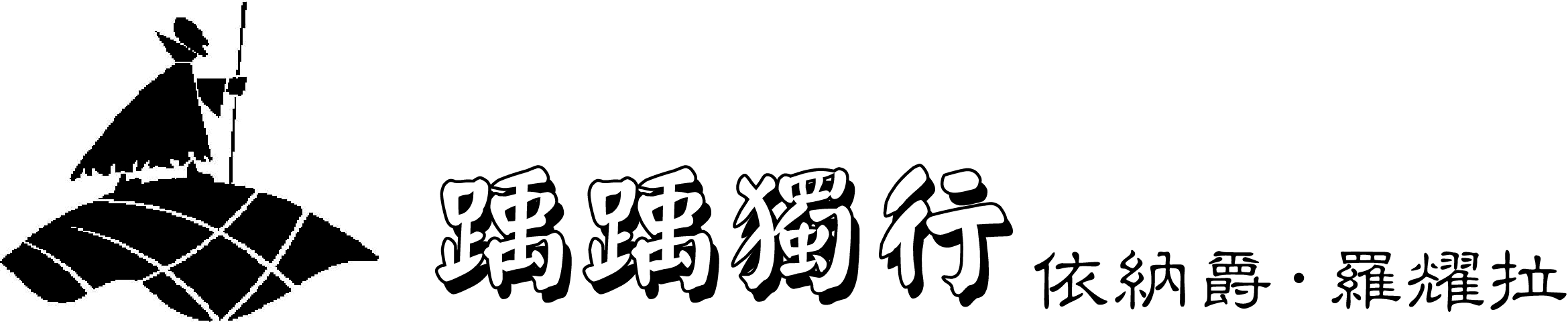 (譯自高伯仁神父共七十章的Alone and on Foot) (續前) 第三十四章:一起規劃未來,1534年 徹底奉獻 一五三三年,巴黎國會頒布,只需兩人作證指控,路德派信徒便要接受審問、定罪並處以火刑。隨後的一五三四年,亦在凶兆下展開:法國國會禁止對聖經作任何新的法文翻譯,並通過了一條要徹底剷除異端,全面捉拿異端分子的新法令。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依納爵帶伯多祿•法伯爾做神操,希望藉此鞏固他與法伯爾之間的關係。法伯爾是團體中第一個接受神操的成員,並在幾個月後,領了聖秩聖事,在一五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舉行首祭。稍後,其他所有成員都個別做了神操。這次神操不是引導他們皈依,而是選擇或確認一種生活方式,因為每個同伴在開始做神操之前,對自己的未來都已經有了想法。正如依納爵在薄薄的《神操》裏,第五條凡例中所說的:「奉行神操的人,如果開始便以慷慨的心胸,將全部意願和自主奉獻給自己的造物主,聽憑祂隨意處理他和他所有的一切,為能最好地侍奉祂,這樣一定為他很有益處」(《神操通俗譯本》,侯景文譯,#5)。古往今來,許多宗教人士都遵行了這建議,但誰會比這個團體更認真呢?他們成了依納爵測試他技巧的實驗品,目的是為栽培一個人發揮他的最大潛能回應天主的寵召。六個同道一個接一個,做了神操。為了這次神操,其中五人離開了住所,搬到一間小房子,專注祈禱,克己守齋,長期禁食。依納爵常常探望他們,以作跟進。鮑巴第拉是唯一一個留在學院裏,在自己房間做神操的人。 家事 一五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依納爵獲頒文科碩士學位,這是為了社交上的便利,而不是因為野心或虛榮心。他被收錄為潘普洛納教區神學系的依納爵•羅耀拉碩士。依納爵多年沒與家人聯絡,一五三二年六月大概為了回覆他哥哥的一封信,他嘗試解釋他的經歷:「你說你很高興,因為看來我在沉默良久之後,再給你寫信。請不要驚訝。一個受了重傷的人開始使用一種藥膏,在療程中改用另一種藥膏,最後又用另一種。同樣,在我的情況,起初用一種藥膏是必須的,然後是另一種,最後又是另一種」。他寫這封信是為警惕迷戀世俗事務,醉心於社會成就的家人,是為讓他們品嘗一下靈性的事,向他們傳達做有永恆價值的事的重要性。對依納爵而言,血緣關係不再重要了,他放開懷抱,迎納眾生。縱使他們是罪人都是一樣,只要他們承認。他關注他們的永恆歸宿,認為他們自己更當時刻關注。 做什麼呢? 一五三四年夏天,這群摯友圍在依納爵身邊,從容不迫,認真地仔細考量和商討未來。他們不急於做任何決定,因為其中一些人將要開始讀神學。不論未來會怎樣,眼下他們專注於特定幾點:他們選擇過實貧生活,預示了為過這種生活方式,他們需要放棄一切;助人是他們的使徒工作,但不收酬報;一旦完成學業,貧窮的生活方式,會更徹底。 他們選擇過獨身的守貞生活。他們絕對不是憂鬱的苦行生,而是基督喜樂和忠誠的追隨者。這位基督是他們通過神操認識的,並想在耶路撒冷追隨祂的芳蹤。他們每一個都應承參與這次朝聖,這個承諾成了把他們彼此連在一起最明顯、最具體的環。至於應該如何進行,他們之間當然有不同意見,但他們草擬了一個行動計劃。他們會繼續各自的神學課程,然後在一五三七年,離開巴黎到威尼斯。到時,也許他們需要用一年時間等候乘船往聖地的機會。但是,如果去耶路撒冷的門不向他們打開,他們會把自己交給教宗,任他安排。如果他們成功抵達耶穌的故鄉,到時他們會再作決定是否永遠留在那裏,或全體折返。如果他們選擇歸來,他們會接受教宗的任何指派。 大概就是這個對未來的展望,把他們組成一個團體,也是第一次各成員把自己的命運交託在團體手中。耶路撒冷是目的地,另一個選擇是羅馬,但是羅馬僅僅是依納爵夢想的替代品,他沒有意圖去征服基督宗教的首府。如同他對摩爾人所作的一樣,依納爵將疆繩放鬆,因為他知道「有一位」正在指引他的腳步。  第三十五章:聖願與忠誠,1534年 在致命山發聖願 「在巴黎期間,我們還沒有建立修會的意願,只想藉貧窮的生活、宣講和在醫院裏服務,獻身侍奉天主並幫助近人」,多年後雷奈士這樣說。確認他們所作的決定的方法:依納爵和其他六位同伴,即鮑巴第拉、法伯爾、雷奈士、勞德理格、撒爾墨龍和沙勿略,於一五三四年八月十五日聖母蒙召升天節,在巴黎市郊,致命山的聖德尼聖堂,由他們唯一領了鐸品的法伯爾主持彌撒。領聖體前,他們逐一宣發聖願,法伯爾隨後也發了聖願,同儕的承諾遂添了神聖的一面。四十年後,其中一位健在的成員,回憶起這次「全燔祭」,或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的誓願,仍難掩激動。他們的聖願包括以下的要素:為鄰人謀幸福;過貧窮生活;去耶路撒冷朝聖;如果不能如願朝聖,就把自己交在教宗手中,任他派遣到他認為是最好的地方。 一五三五年和一五三六年的聖母蒙召升天節,他們再到致命山,重宣聖願。兩次依納爵都不在。雖然如此,團體添了三位新同伴:薩瓦人克勞德•傑伊,兩位法國人巴斯卡斯•布諾特和桑•庫杜萊。那時,團體已有十位成員,但對未來仍未清楚。一五三七年,正在威尼斯尋找船隻載他們去耶路撒冷的依納爵,給在巴塞羅納的一位朋友寫信:「我不知道我們的主、天主給我預備的是什麼樣的未來」。一五六三年,納達爾這樣描寫處於那個階段的依納爵:「他正慢慢地被帶往他未知的將來,他不是在考慮成立修會」。 「另一個人」 一五三四年九月,沙勿略終於有空做神操了:他退到一間隱蔽的小房子裏做,依納爵常來看望。有時獨自一人到訪,有時與一位同伴同往。沙勿略為了補贖他想作運動員的虛榮心,用繩緊緊捆綁自己的手和腿,以致手腳都不能動,直至肌肉壞死,幾乎要截肢,才作罷。儘管這些行為過了分,但神操對他是個意義深遠、無法忘懷的經驗。沙勿略出靜後,如往常一樣快快樂樂,但已變了「另一個人」。他的《神操》小冊子從此未離開過他,因為它塑造了他的生命。他熱誠地敬愛依納爵,把他當作「在基督的深愛內唯一的父親」,因為他感激依納爵的指導,讓他經驗到天主和他心連心對談。  宗教戰爭 宗教戰爭一五三四年十月,所有「主內的朋友」繼續他們的學業。依納爵在一個道明會中心,學習聖多瑪斯的學說,因為依納爵對他總是懷著最深的敬意。同月,基督新教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的牆壁,張貼抨擊彌撒的標語。十一月,第一批路德派的人被判死刑:他們的舌頭被刺穿或手被砍掉,然後被綁在城市廣場上的火刑柱上燒死。一五三五年初頒布的法令說,任何人企圖收藏一個路德派的人,將遭受同樣的刑罰;凡把路德派的人移交當局,都會得到獎賞。勢不兩立的雙方就這樣引發一場戰爭,對教義所持的立場,必須清楚準確。 在巴黎,觀點之爭的風暴,教依納爵認識到,使人們藉神操與基督面對面相遇之前,他必先要為他們提供一些指南,使他們可以掌握方向。迄今,正如我們在之前說過的,教會就像他每天生活不可缺的空氣,或像母親的大腿;生活在教會自然而簡單,就像呼吸或保持健康。他生活在教會裏,不懷疑教會,對教會權威或傳統的虔誠敬禮,沒有不滿。不過現在他必須承認,擺在眼前的「慈母聖教會」,是一個有污點的教會,是一個在「戰爭中」的教會。 忠於教會 儘管教會世紀以來,背負著沉重的包袱,依納爵相信,教會仍然是「主基督的真正淨配」。這不死的原則叫他在《神操》中,寫下「與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他相信,人總可找到批評教會的理由,但也可找到為她辯護的一大堆理由。這不是說,相信就要盲目遵守法紀。「與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跟《神操》所載的其他規則一樣,是為給那些參考並應用他的《神操》,給別人講授者,有所依循。寫下這些規則的原意,是為保證《神操》作者的正統性。這些規則在不同年代,不同地方都鏗鏘有聲,都可以幫助我們處理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在戰爭中的教會,應持的正確態度」。 路德和伊拉斯謨所持的是跟這些規則對立的態度。對於告解聖事、彌撒、日課、修道生活、聖願、獨身制、婚配聖事、對聖人和聖髑的熱心敬禮、朝聖、大赦、守齋和做補贖、四旬期禮規、祭衣和保密制,路德的態度是摒棄,伊拉斯謨是大肆抨擊,依納爵卻嚴肅待之,讓它們成為自己實踐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簡單地說,我們應該稱讚而非詆毀,更不該抗拒。至於代表教會的一些人物,他不打算為他們不可辯護的行為作辯護,卻尋求方法去糾正,不傷害他們的聲譽。 依納爵側重教會的訓導權,不是因為他固執或膽小。日後,他會讓人看見他創新的程度,令許多人無法接受。他的《會憲》是靈活的,可適用於特殊的生活境況,且經得起時間考驗。他推崇教會訓導的明確立場,是由於他對基督的信仰,以及他渴望永遠在聖神持久而活躍的臨在中,做基督的「真正淨配」。  (待續)
© Copyright Shalom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