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怎樣利用《和平》祈禱? |
| 《和平》首頁 |
| 本月份《和平》目錄 |
| 訂閱《和平》 |
| 二零一三年 九月《和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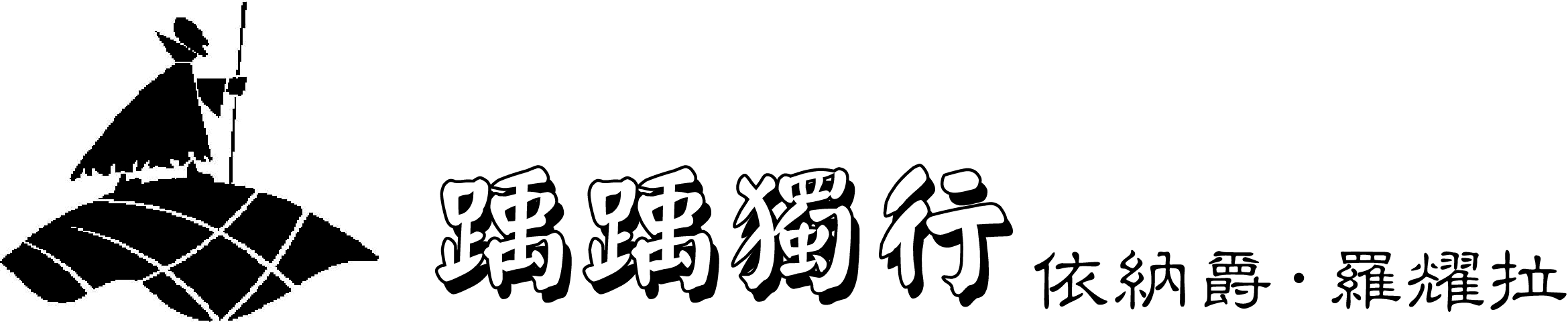 (譯自高伯仁神父共七十章的Alone and on Foot) (續前) 第十四章: 生命的改變,鋸山,1522年3月 告解 依納爵在做武裝守夜前,「用了三天時間寫下 自己的罪過,並辦了總告解」。他給聽告解的神父 桑o查隆分享了他一直沒有向任何人透露的、他想過貧窮生活的意向。桑神父是位聖善的法國隱修士,他不領教會俸祿,所以,他對慷慨放棄大量財產是什麼一回事,亦懂一二。桑神父有能力去理解並指導這個新來的、充滿熱情的朝聖者,他的告解絕非雞毛蒜皮的事,亦不是循例。 審慎的桑神父知道,他正在輔導一個慣於將讀到的書中內容實踐的人,這人正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桑神父可能送給了依納爵一本他常送給識字的朝聖者,講解有關罪的彙集,又或者送了一本隱修院的珍藏 茨斯尼若斯著的《靈性生命的操練》 給依納爵。這本書強調有系統的步驟,在靈修進程的重要性,特別是如何祈禱。 學習祈禱的方法 依納爵非常清楚,要馴服一匹馬、學習演奏樂器、拉弓引箭及寫得一手好書法,都有一套方法。現在他將要學到,要走的路不是特異、毫無關連的英勇行為,而是由內在進程組成的一條煉路、明路和結合路;總告解不是這過程的結束,而是開始。他將會學到怎樣去省察良心和將精神集中;而且祈禱是可以學習的,例如在開始祈禱時的呼求,怎樣運用想像力,及依循步驟去作反省;這樣,自然就會產生對禱或跟天主的交談。只是知道這一切是不夠的,他必須耐心操練。這是一個啟示,一個真正的發現,這給依納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開始在筆記部中,草草記下他的心得;後來他稱之為《神操》,其結果有目共睹。  往茫萊撒 往茫萊撒身穿麻布衣,依納爵於一五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在聖母祭台前徹夜祈禱。麻布衣裳成了這位騎士的新徽章。他隱沒在朝聖的人群中,藏身於教堂的隱蔽處,領了聖體。「黎明時分,他離開了,免得被人認出來」。他沒有取道去巴塞羅納,「因為那裏他會遇到許多認識他並尊敬他的人」。他改道而行,到了一個小鎮 茫萊撒,並決定在這裏的一個收容所住幾天,「以便在他小心翼翼攜帶的書中,寫下一些筆記,此書是他獲得莫大神慰的源泉」。他在短短的時間內體驗的事情太多了,他需要停下來,通過寫筆記把自己的情感傾吐,這本筆記是他背包中唯一的寶貝。 清白的乞丐 依納爵總沒想到,他留下一場風暴。他的一切掩飾和提防都沒有作用。有人追趕上來,認出他就是那些華服的主人,便緊張地問他是否真的把衣服給了那個窮人,正如那乞丐所說的一樣。那個乞丐竟然如此急於冒充富人,如同依納爵急於充作窮人一樣!依納爵講了事實。他感到沒必要說明自己是誰,從那裏來,或家族的姓氏 即使可讓那個清白的乞丐得到釋放。依納爵簡單答說:「衣服是我給他的」,並「滾下同情的眼淚」。依納爵在《自傳》中記載:「他同情那個接受他贈衣的窮人,因為別人以為那些衣服是他偷來的,因而磨難他」。 就這樣,在他一開始隱姓埋名,獨自深入默想的首個小時裏,便發現一個不知名的鄰人,無辜被捲入事件,徬徨無助。一個能夠鋸掉自己的骨頭而沒啜泣,只攥緊拳頭的人,現在卻因為同情別人而灑淚。儘管他的哭泣極可能與正統的騎士精神不符,但為我們瞭解依納爵的心,卻極富意義。 「朝聖者」 現在我們的朝聖者從鋸山下來,只是想成為一個基督徒,真正學習做個基督徒。他仍然想一意孤行去行善,只想靠自己的決定去幹一番偉業,而不是去忍受或體驗。他想通過捷徑成聖。依納爵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揀選的器皿」,但他從來沒有懷疑「該受多麼大的苦」(宗9:15-16)。他仍有許多事需要去學習,但他決定展開「一個貧窮基督徒的歷險」。他想做個很窮的人,窮得連名字都不要。他的名字不再是眾人皆知的依尼高,而是依納爵,更非羅耀拉家族的人。他只是一個朝聖者,一個無名的基督徒,一個沒有姓氏的基督徒;但他並非沒有身分,並非沒有基督徒的熱情。在整部《自傳》中,他把自己簡單地稱作「朝聖者」。  第十五章:依納爵與路德 內在的戰爭 在這個生命階段,依納爵沒有參與家族、國家、教廷的事,也不問政治。西班牙和法國之間的戰爭、科爾特斯征服墨西哥、航海家巴斯克人卡諾環繞地球一週凱旋歸來、穆斯林洗劫貝爾格萊德和羅德斯 這些事情對依納爵都沒有意義,除了它們可能會影響他去耶路撒冷的計劃。當代與他無關。他為完成人生大事而拼搏,且無止境地渴慕那位「絕對的」。新版本聖經、伊拉斯謨和多馬斯o摩爾的著作都跟他形同陌路,只要有《耶穌傳》和《聖人言行》這兩本書的摘錄,他就滿足了。他與有影響力的人打交道,只是為了取得往聖地的通行證。 路德? 甚至馬丁o路德也不在依納爵的世界中。路德在一五二零年被逐出教會,曾在一五二一年四月召開的沃爾木斯會議露面,然後被困在華爾特堡;與此同時,依納爵正在羅耀拉堡療傷,並重新檢視他的生活。由路德翻騰,席捲整個歐洲的巨變泛起時,依納爵正開始他的朝聖之旅。在這位匿名的朝聖者腦海中,從未閃現過要把自己當成路德的對手,或成為整個歐洲反基督新教力量的組織人,或成為革新天主教的遊俠這些念頭。當路德嘲笑,認為發宗教聖願不合人情及違反福音教導時,依納爵自由地發了貞潔願。他很簡單,他是依納爵、一個無名的朝聖者,而路德的名字卻響遍整個歐洲。 革新教會,抑或革新自己? 路德比依納爵年長差不多十年,並且在他選擇畢生要走的路上走了很遠;相反,依納爵剛起步,穿著麻布衣,一腳穿著涼鞋,一腳光著,緩慢地一路前行。路德迎頭攻擊教會,無情地反對教會,與教會決裂 這一切都是以福音的名義而作;依納爵沒有走出去革新教會,他走進自己,尋求革新自我。他是個安靜的人,懂得在適當時刻在耳邊細說重要話語的大師。他不判斷,甚至可能沒有時間去想教會的事。他認識到,一切事能夠並且應該是好的,而壞事往往來自我們不當的選擇。對依納爵而言,教會就像瓦遮頭,或像母親溫暖的膝蓋,或像空氣,人呼吸但不會時時刻刻問空氣是否受污染。 相似之處 依納爵與馬丁o路德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是隱居的英雄,都充滿熱情,都被強烈的內在經驗所引誘和征服。路德在隱修院的塔上潛心修行,依納爵在茫萊撒的斗室默觀祈禱。他們的內心世界,日夜將他們時刻吸引,耗盡他們的精力。他們的自身經驗比任何理論知識都強,從經驗中他們陶成各自的信仰。他們都有某種詩樣情懷,都能坦誠反對虛偽,都能慷慨付出,毫不計較。他們各自都有犯罪的經驗,及深入肺腑的自我厭惡,但這促使他們更嚮往期待已久的平安,即由他們的信念結出的神慰碩果。在依納爵生命的某個時期,他會非常理解路德所說的:「我反叛的肉身以一種吞噬人的烈火,燃燒著我。我本應是靈性的獵物,卻被肉慾、情慾、懶惰、閑散和麻木遲緩所支配」。撰寫路德生平事蹟的一位法國作家說,喜歡獨處而孤獨的路德最需要的並不是訓導,「而是靈修生活,內心的平安,一種能釋放他的肯定,及在主內憩息」。這些說話同樣可用在依納爵身上。 信德與功德 依納爵與馬丁o路德都把他們的道變成一種普世教導,因為他們深信,決定性的戰爭是發生在人的內心,而不是在制度裏。而且人的心因著痛苦和渴望,都是相似的。 路德與依納爵都將那帶給他們喜樂的發現廣泛傳播;路德通過印刷品大聲宣揚,依納爵在靜寂的角落與人面對面傾心交談。兩人都堅定不移,非常自信,且具煽動力,各自都投下戰書:路德抗衡羅馬教廷,依納爵勇敢地面對宗教裁判所。兩人都是熱心的基督徒。路德視基督為給予我們一切的救贖主,依納爵絕對同意,但他知道基督要求我們的不僅是信德:基督要求我們跟隨祂,效法祂,侍奉祂,甚至將我們的意志奉獻給祂,即使我們的意志非常薄弱。 假如今天路德和羅耀拉對他們的遺產進行盤點,他們很可能會問自己同樣的問題:「我的事業和我的追隨者是否都忠於我原本的慷慨大計,忠於我那首次與耶穌基督的真正相遇,那充滿幻想和真誠的初戀?」。  (待續)
© Copyright Shalom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