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怎樣利用《和平》祈禱? |
| 《和平》首頁 |
| 本月份《和平》目錄 |
| 訂閱《和平》 |
| 二零一五年 十月《和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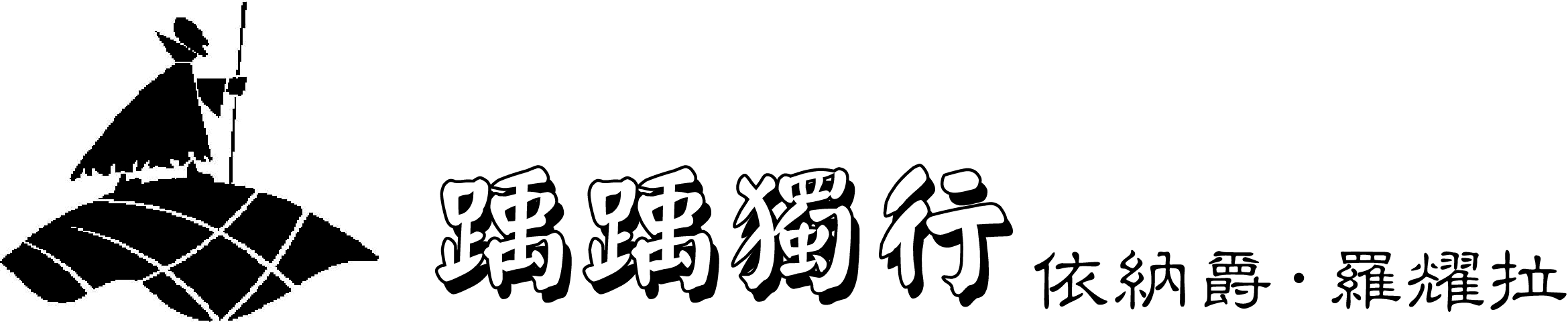 (譯自高伯仁神父共七十章的Alone and on Foot) (續前) 第五十八章:忙碌的神秘經驗者 眼淚的恩典 依納爵的《靈修日記》讓我們知道多少,他深邃的神秘經驗,主要是他在奉獻彌撒聖祭時,對天主聖三的體驗。這位含蓄而沉默的巴斯克人,因為謙虛純樸,所以更難去表達所有神秘經驗者都認為是難以形容的經驗。基本上,我們可以說他把秘密帶進墳墓去,雖然我們可從這些寶貴記錄中,得悉他的秘密和性格點滴,知道他是個充滿神恩,是個始終在聆聽天主的人。 在依納爵筆下,每個字都粗糙樸實,像採石場出土的花崗岩,靜靜地散發巨大能量。他談到「深情奉獻,內在和外在眼淚」;「我所領悟的,我無法形容」;「我深深地明白到非常屬靈的,令我喜悅,感覺溫馨,心神灼熱,十分甜美」。他不僅在獻彌撒時,感受到神秘的經驗,他走在街上,或坐在餐桌,或在樞機的接待處等候,都會有這種經驗。他的神秘經驗沒有影響他的日常工作,也沒有令他尋求過一種比較退隱獨居的生活。這些經驗也沒有呈現出一種婚姻象徵 ─ 這是眾多其他神秘經驗者的經驗特徵。在這裏,神秘經驗化作服務,他傾慕和愛惜的真理,變成一種動態,成了他淚流不止的泉源。有誰相信,一個有無窮精力的行動巨子,眼睛卻被神秘的眼淚毀傷!他在《靈修日記》中,共一百七十五次,提到眼淚之恩。沒有畫家能夠繪畫藏於死亡面具背後,現今已是死寂,卻曾經會說話的眼睛。在巴都亞,有人這樣形容:「那個身材矮小,腳有點跛,目光炯炯的西班牙人」。依納爵的確很矮,這說明了為什麼在他去世之後幾年,一個講道員將依納爵的偉大與他不吸引人的外貌相比時,說他是「一顆穀粒」,「那麼矮小的一個人」,「天主的小夥子」。 陶鑄會士 雖然是個神秘經驗者,依納爵的生活踏實,將精神投到數以千計的平凡任務和刻板的日常工作,忙於各種使徒服務,特別是他認為最重要的 ─ 陶鑄他的會士,建立初露曙光,但已經是「四散」的「微末修會」。他需要為修會制定指南,也需要凝聚派到世界各地的會士,使大家保持團結。依納爵務實具體,不喜歡抽象或含糊的概念。接受他口述他的《自傳》的卡馬拉,這樣形容他這個特徵:「他從不煽情,只以事實來說服……他決不用言語修飾事實,他細緻地將全盤實情擺明,就幾乎足以令人折服……他講話的風格簡單、清楚明瞭。他對過去的事情有特強的記憶力,甚至對某件事的一些關鍵話也記得一清二楚。他可以告訴你十年前或十五年前,甚至更遠之前所發生的事,準確得就像當時發生一樣」。對依納爵,就像對任何一位真正的巴斯克人來說,言語舉足輕重,因為言語傳達一個人。這是為什麼,他長時間反省過他想說的話,才講才寫。 明白人的心理 二百多條的指引,幫助我們瞭解依納爵的個性和行事方式。這些指引展示耶穌會早期使徒工作的廣闊範圍和多樣性,其遍及的地域和成就。不過,最特別的是,它們給我們舉例說明依納爵的個人標準、動機、目的和激勵他做一切事的熾熱福傳精神。此外,我們從中看到一個善於與人打交道的一流心理學家。一五四一年,當他派布諾特和撒爾墨龍去愛爾蘭執行極棘手的使命時,給了他們一些具爭議性的建議。他們要少說多聽;當他們與有影響力的人交往時,要打量那個人,並遷就那人的性情,就像聖保祿宗徒為每個人成為一切一樣。他建議他們要接納他們希望影響的人的方式:那就是,他們要通過自我反省來武裝自己,下定決心容忍一切,保持沉著冷靜。他們要箝制口舌,切記私下說的話最終會公之於世。他希望他們能慷慨地用時間去幫助每一個人;如果他們許諾明天要做什麼,那麼今天就做。「為了捕獲人去更好地侍奉天主」,他們要從那人的門進入,從自己的門出來。 愛爾蘭使命失敗 儘管語重心長,忠告一翻,一五四一年的愛爾蘭使命,仍以失敗告終。在里昂,撒爾墨龍和布諾特跟蘇格蘭人畢頓樞機會面,他同時是總主教及六名孩子的父親,四年後,他在臥室被同胞砍斃。畢頓告訴羅馬教宗派來的這兩位會士:在全人類當中,也許愛爾蘭人是最野蠻最沒自律的人。他的話也許對他們有些影響。不管怎樣,他們在愛爾蘭留了一個月。當時愛爾蘭三十個教區的二十二名主教已經不承認教宗的權柄,轉為支持亨利八世。事實上,有人認為兩位會士能夠活著離開愛爾蘭已經近乎奇蹟。穿著骯髒而破爛的長袍,在返回羅馬途中,有人懷疑他們是間諜,把他們關進里昂監獄。撒爾墨龍這樣寫,並沒有誇張:「在愛爾蘭不乏分擔主基督十字架的機會,我們捱飢抵渴,沒有枕頭的地方,甚至連安靜地念一篇《天主經》的地方也沒有」。  第五十九章:指示與信件 脫利騰大公會議 依納爵派雷奈士和撒爾墨龍去參加脫利騰大公會議,給予重要的忠告:他建議他們不但要為自己,熱切祈禱,更要引導別人一起為會議取得成果而祈求。他勸他們要耐心聆聽,謹慎處理具爭議性的問題。只要是為脫利騰人民服務,就不得怠慢或尋求自身的舒適。他們要宣講,聽告解,教兒童教理,給人帶神操,探訪醫院的病人,勸人要熱心要多祈禱,幫助他們更認識自己和更愛天主。他們要「懷著愛心親切地、入微地、實際地」鼓勵每一個人革新靈性生命。他們之間要和睦共處,要以手足之情互相規勸,互相糾正,每天一起訂定和修改日程。 依納爵派會士出席脫利騰大公會議,「不是因為他認為他們可以貢獻什麼,而是出於服從」。可是,當他們在一五四六年五月十八日到達之後幾天,他們的名字被列入神學家的名冊。不久,兩人就介入了會議,成為矚目人物。在大公會議的下一個會期,即一五五一至五二年間,他們的名字被列入宗座神學家的名冊。不過,這無礙他們繼續住在狹小、骯髒陰暗,只有一張?的房間。這房間連供閱讀和書寫用的桌子也沒有。他們再次介入會議的討論,卻沒有因此放棄鍾情的使徒工作 ─ 聽告解,講教理,探訪醫院的病人。他們出席大公會議,使很多人認識到這個新成立的耶穌會。從那時起,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有更多的主教,歡迎耶穌會士到他們的教區。 沒足夠時間吃飯 兩位前巴黎大學碩士令人矚目的,不僅是他們的神學知識,也是他們的生活質素和對使徒工作的熱愛。他們打動人的秘密在於他們的司鐸職。他們是真誠的、有效率的司鐸,履行傳統的牧職,即兩人住在一個住宅或房子裏,一起從事固定的使徒工作,或兩人暫駐於某個城市。與別不同的新鮮事,是他們的一絲不苟,落力地去做牧民工作,而這些工作,不幸地是當地神職人員忽視的。依納爵和他的追隨者,堅持要做到深入每個人的心及他們的文化。他們勉勵已經準備好接受天主的人,亦沒有遺忘沒得到關懷照顧的大多數。他們能夠一整天坐在告解亭聽告解,幾乎沒足夠時間吃飯。他們播下的種子落在民眾身上,落在開始進行改革的隱修院,落在想深化靈修生活的個別心田。他們的付出改變了許多司鐸和蒙席的生活;他們吸引了慷慨的青年加入耶穌會,鼓勵了平信徒參與他們從未考慮過可以投身的服務。他們更設法確保他們開展了的工作,在他們離開之後能夠持續。於此,我們無法辨別哪些是他們事先計劃的服務,哪些是他們對即時的基本需要而作的回應。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遺餘力,慷慨奉獻自己,直到筋疲力盡。早期的會士離開總會院這個大家庭,分散到各地,生活充滿各種各樣的磨難,但每人都精彩地活出對責任的承擔。 保持聯繫 甫開始,耶穌會是一班親密的朋友一起去闖,彼此相處簡單直接,沒矯揉造作。例如,沙勿略有一次在羅馬,使一位客人吃了一驚,因為他簡單地喊說:「嗨,依納爵,亞老茲來了!」隨著會士人數增加,他們很少機會碰面,這種無拘無束的深厚情誼,只能靠十六世紀緩慢的郵遞維繫,讓大家互通消息,知道大家仍在持守著同一的生活方式。依納爵向他的會士堅持,寫信不是消遣,而是責任。他以身作則,用榜樣帶頭:我們保留著他大約七千封信,但他所寫的遠不止此數。在一封信中,依納爵說,他在一個晚上寄出了二百五十封信。他費心竭力,在用字遣詞方面,精雕細琢,寫了又改,改了又寫。他給會士們的準則是:「寫要比講慎密,因為書面文字會被保留,成了永久的證據」。 依納爵的信件透露了他的心思和個性:他寫下他最優先考慮的工作重點,他的顧慮和他怎樣奮發面對困難和反對。讓我們看見他從善如流,有情有義,感恩戴德,千般忍耐。他?述,勸告,建議,呼籲,命令。他設計驚人的行動,例如:向土耳其發動聖戰。他給每個收信人莊重地、有禮貌地寫信,結語總是充滿感情,並仰望超越的天主:「願天主喜歡我們明悉祂的聖意,並圓滿地將它實現」。明悉主旨並將它實現:兩者都是達至真正皈依不能缺少的要素。 情牽萬里 依納爵很依賴他的秘書朴蘭考,助他維持沙勿略稱之為「愛的修會」的團結和成長。他派會士去遙遠的地方,獨力進行充滿風險的事工,很想聽到他們的消息,也希望他們大家互通消息。他曾經說過,他甚至想知道咬他的兒子們的蝨子這種小事。由此可知,他是多麼想知道他們的辛勞、成功與失敗。收到會士的消息會帶給他最大的喜樂,特別是沙勿略的來信。沙勿略是這樣簽署他的信件的:「放逐到最遠,你最末的兒子」。來往他倆之間的書信,足足需要兩年。沙勿略含著眼淚,跪著讀依納爵的信。他珍惜依納爵這樣說:「完全是你的,沒有一刻能忘記你的,依納爵」。他把依納爵和其他遠方同伴們的簽名,當作祝福,戴在脖子上。  (待續)
© Copyright Shalom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