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怎樣利用《和平》祈禱? |
| 《和平》首頁 |
| 本月份《和平》目錄 |
| 訂閱《和平》 |
| 二零一七年 二月《和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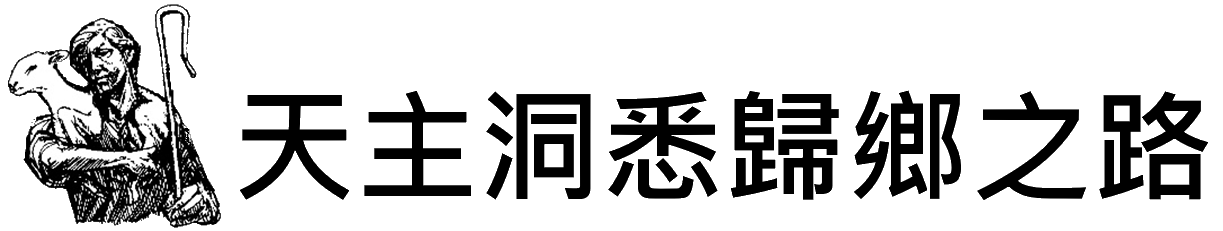 (譯自耶穌會士柏德•奧蘇利文神父 Fr Patrick O’Sullivan SJ 共七章的 God Knows How To Come Back Home) 第四章 內在的黑暗 (續前) 就此,我想提出一個警告。我們務要提防,切勿為逃避痛苦,而將我們所受到的傷害「精神化」。有人口裏會說「奉獻於主」、「這是天主的旨意」這類說話,以作逃避,而沒有真正去面對和接受痛苦。在這些情況下,跟耶穌交談肯定是重要的;如果我的祈禱是真實的,我會告訴耶穌真正在發生的。可是,我不能告訴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除非我面對和接受我當下痛苦的現狀。 我不會讓大家有一個處理複雜麻煩的人際關係,常是簡單直截的印象!事實絕非如此!有時我們會發覺自己處於一個要非常小心提防的境況,但我們又怕自己顯得刻薄,怕自己在批判。 我的一位朋友喜歡說:「你不能從水喉得到香檳」。舉個例說,如果有人出賣了我們,令我們不能再信任,而他們又毫無承認的念頭,若然重新投以信任,為我們自己或為他們都不會有用。因為這就是強求他們到達一個他們未能達到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有用的就是留意並分辨清楚自己是在作判斷,還是在肆意批判。 我們要判斷他人及他們的行為;否則,我們就像一塊海綿,只吸納,無作用。作判斷是健康的。肆意批判則另作別論,因為已超出了判斷 ── 是一種不但將人看扁,兼把人放入一個箱裏,並把蓋封好的態度。自以為是,無惻隱心,就會衍生這種態度。 讓我舉個例子。但在舉例之前,我想先反省一下耶穌及祂的使徒工作。早前,一位耶穌會士跟我說:「耶穌以憐憫取代潔淨的儀式」。他繼而解釋說:在耶穌的時代,宗教領袖們非常強調要行潔淨的儀式 ── 如堅持在進食之前,人要將自己及所有廚具餐具洗乾淨。看見五千人餓著肚子,耶穌動了憐憫的心,就地使他們飽餐,不在乎食前先要潔淨自己。 行潔淨儀式,除了是給人民負加重擔,另一壞處,是它隱藏著一種自以為是的態度。嚴守了儀式的人,因擦亮了自己的外表而驕傲,以為自己聖潔過人,而瞧不起沒嚴守儀式的普羅大眾,對他們只顧鄙視,不加憐憫。 不幸的是,這種潔淨的儀式,在今天仍然常見;取而代之的現代形式是「自以為是」。許多人都很容易陶醉於自我的形象,不惜一切都要讓自己的這個形象在人前閃耀 ──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明,我要舉的例子了。 許多年前,當修道生活開始受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影響不久,我負責培訓有意成為耶穌會士的修生。界線變化得很快。有一次,我認為一位修生越過了仍然生效的界線,遂將他召來,在一眾修生面前,盡情地教訓了他一頓。之後,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感覺不安,思前想後,懷疑自己是否做對了。我自覺錯了,於是我去找那位修生道歉:「很抱歉我在其他修生面前這樣教訓你」。他說:「我實在覺得你反應過敏了」── 我立即火爆,又教訓了他一頓! 多年以後,我才真正瞭解到發生了什麼。在我第一次對修生發火之後,我感到的不安與他無關。我的不安是由於我在眾人面前大罵 ── 有失院長風範!── 我彷彿毀了自己的形象。我想,要修補我的形象,我要表現謙卑,並且要道歉。這是真正的動機,而非同情那位修生的感受。如果我真的關心他的感受,我不會在短短十分鐘內炮轟他兩次! 讓我們返回起點。作出判斷和肆意批判的分別,是判斷有憐憫的餘地,批判是放縱我們的自以為是 ── 沒有憐憫的餘地。 儘管這個分別能幫助我們,我們仍會發覺,有時雖然我們想憐憫,卻又怕與某人有任何密切的交往。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與這人交往,只會消耗我們的精力。我們很容易陷於擔心我們「應該」做什麼。 與其尋尋覓覓好看得清晰,而清楚的答案卻又似乎常在躲避,我發覺最好還是直接把事情放在耶穌手中,對祂說:「耶穌,請賜我憐憫之恩;祢願意我以什麼態度去待這個人,就請祢將這種態度賜給我吧!」這樣做,我們就是放棄任何隱藏在我們內的計劃,將空間騰出,讓耶穌做祂認為是最好的。 除了馬天尼樞機提議的哀禱,處理過往的傷痛事件,還有一個方法,這是關於傷痛我最後要說的:在最近,每當過往的傷痛事件突然湧現,我會這樣應對:「嗯,我很高興一切都過去了」,接著我會把事情拋諸腦後。 我開始明白到,任何過往的事件,若然每當記起仍帶著絲絲傷痛,這就顯示我仍未把它處理好。所以,現在每當這類事件出現,我會重溫,我會將它變成是一趟信仰的旅程 ── 我會帶耶穌或聖母在我身邊。 我發現如果我獨自回顧事件,我只會被吞噬,痛苦或不適全都回來了。但如果我化它為信仰旅程,帶同耶穌或聖母在身邊,我發現我可以懷著希望,甚或信心,進入事件。耶穌或聖母的臨在不但安慰我,且有救贖功效;只要我不隱瞞,盡地告訴他們我心裏的感受,他們就都成了這經驗的一部分,而他們的臨在能夠醫治。當然,這不會突然發生;但它會發生。所以,每當過去的傷痛浮現,將它驅逐是錯誤的,因為它仍抓著我們。邁向痊癒和自由之路,就是返回過往 ── 但必須是個信仰旅程!
要確保我們返回過往的痛苦事件,確是趟信仰旅程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以耶穌醫治人或寬恕人的聖經片段作祈禱。耶穌復生拉匝祿(若望福音11:1-44)是一段我們可重複使用的非常有用的經文。如果我們感到一些過去的事件像壓在心頭的石塊,或每當憶起還是愁腸百結的時候,我們可以停留在耶穌的話,並請祂向我們說:「挪開這塊石頭……解開他(她),讓他(她)行走罷」。 我們的個人文化 我們都知道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 ── 一種特別的行事和交往方式,藉此表達共同的價值觀並讓人在生活中找到意義。廣義而言,不僅國家有其獨特的文化,團體、家庭,以至個人,都是一樣。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文化,與眾不同的言談舉止、習慣、說話模式、看待事物的方式等等,合起來構成我們的個人風格,使我們尋找和表達意義和價值。 我們體諒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我們知道在一個文化當中尊崇的,在另一個文化未必是恰當的。 例如,在某些文化中,說話時,若卑輩定睛看著長輩,便是最不敬的。 然而,不幸的是,在個人層面,我們則沒有那麼通達與寬容,未能生動地意識到存在於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的文化上的分歧。我們往往在想,甚或批評別人的行為,說:「我永遠都不會這樣做!」或「我不明白她看上他的什麼……」。這些例子不可勝數,而我想表達的,其實很簡單 ──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個人文化,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並避免將它強加於人,那麼,人人的生活都會好過得多(更快樂得多)! 由此可見,文化在我們的生命中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實上,無論在團體或個人層面,文化都是培植天主奧秘的土壤。正是在這個背景,福音挑戰每一個文化,並將它救贖 ── 如果文化能開放去迎納奧秘。換句話說,文化是體現天主奧秘的地方,也是困難出現的地方;因為,例如:如果一個人的文化是非常死板的,奧秘便被封閉而非化身成人。 我們怎樣去認識自己的個人文化,怎樣去察看究竟我們是讓奧秘化為血肉,抑或將它封閉?我懷疑內省是否就是答案 ── 我們的個人文化跟我們自己太密切了,令我們看不見。唯具體的場合會給我們揭示我們的個人文化,讓光明或黑暗顯現。讓我們看看一些實際的例子。 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是實話實說,抑或砌詞狡辯?耶穌說真理會將我們釋放,使我們獲得自由。所以,如果我們如實直說,即使別人不同意,我們都會嘗到自由的滋味(即依納爵所說的「神慰」)。當然,我們值得注意別人的可能不同意,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內心經驗到的平安。這種自由的經驗標誌著我們的個人文化給奧秘騰出了空間,真的讓它成為血肉。 反之,如果我們在砌詞,我們的內心會經驗到一種「繃緊」。這繃緊的感覺會隨他人的不同意而加劇,也隨他們的認同而消散。繃緊一出現,就是個人文化在將奧秘封閉,而非讓它展露的標記。 幾年前,當我在羅馬住了多年剛回澳洲的時候,一位在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士來探望我,看我是否安頓了。我告訴他我很好 ── 本能地!── 接著,我說:「我確實察覺到困難之一是我有很多事情想做,卻時常被打擾,這實在使我很難安頓下來。」 我的朋友一聲不響,走到我的書檯,撿起一張白紙,畫了兩個平行列,叫它們「甲」和「乙」。他說:「甲列是你現時的情況,和當中許多你所謂的打擾。乙列是你的意願和你想要做的其他事項。但耶穌在哪裏呢?在「甲」還是「乙」呢?」「我想是甲」,我說。他繼續說:「你的心在哪裏呢?」我答:「乙」。他接著說,「好吧,如果耶穌在甲,你的心在乙,難怪你倆不能相遇,難怪你發現很難安頓下來。」 我以為他說完了,感覺到他的話,多過一天之用了,但傳教士就是執著。臨別時,他說:「也許你說的打擾其實是邀請。」 儘管當時尷尬不安,我確實萬分感激我的朋友給我展示我的文化是如何的「繃緊」,及它如何影響著我同耶穌的關係。當我只想著我願意事情怎樣發展,硬要將向我索求時間的邀請看作打擾時,我就是在逐步遠離奧秘的真實臨在,不容許它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 在我的日常文化中 ── 實現。 簡單地說,管用的是:問自己能否意識到,在一天當中,精力的消長。我們都會遇到精神煥發的時候,就像我們都會遇到消耗我們精力的情況。如果我們不能夠察覺這些內在的動靜,便顯示一種相當僵化的個人文化,活活窒息了奧秘給我們的耳語:「這裏有生命;那裏沒有生命」。 如果我們意識到,在一天當中,精力的消長,這便顯示奧秘有空間在我們內活動。我們愈留意這些變化,奧秘便愈有活動的空間,讓我們感覺到它的臨在。 恐懼和焦慮 在耶穌的教誨中,重複出現的其中一個主題是「不要害怕」。恐懼是我們都不會感到陌生的經驗,很多時候恐懼對我們毫無益處,無怪乎耶穌極力叫我們不要害怕。 事實上,我甚至會說恐懼不但能破壞我們的所有關係,且最能損害的,是我們同耶穌的關係。為什麼?因為正如愛將恐懼驅逐於外,反之亦然 ── 恐懼驅逐愛;而天主是愛。 這是恐懼最具破壞性的方面,但還有其他。第二、是當恐懼成了我們行事的動機,這樣,我們就會變得更受恐懼影響。動機推動我們,幾時當我們容許恐懼來推動我們,它只會繼續加強策動我們的能力。 第三、當恐懼成了我們在某個情況中做事的唯一動機,我們的表現就是相當無價值的 ── 無生命的 ── 因為沒有其他動機在工作。情況就像在梅子布甸放少許砒霜 ── 布甸的滋養價值全被毒藥奪去。發號施令的,是毒藥。 許多年前有人請我幫忙做點事,這事本身相當好和合理,只是我感覺不自在。稍作祈禱和反省,我清楚瞭解到,唯一驅使我去幫忙做這事的動機,是我怕得罪對方,更可能會引發一番爭議。我絕對可以看到這事的正面價值,但任何這些正面價值都不能感動我,推動我,因為恐懼令我不能再經驗到它們。 所以我說「不」,經驗告訴我們,一旦受恐懼策動,它只會壯大。況且,很多時候,對方根本不會因此而感到不快! 返回第一點 ── 每當我們因恐懼而行動,讓步的是我們的誠信,即我們同耶穌的關係。如果我們是在跟隨祂,聖神在我們心中總會讓我們知道我們作出了讓步 ── 我們的五內總會有感覺! 我被派駐羅馬與基督徒生活團工作多年。工作涉及不少遠行,有一次,在旅途中,我有機會參予一個靈修輔導的課程。這課程重「體驗」。學員會輪流互相當神師,其餘的人會坐在一旁靜靜的參予,並在稍後提供他們的意見。 事有湊巧,我跟其中一位組員互有齟齬,其他 組員都知道了。翌日輪到我作靈修輔導了,當組長問:「誰願意接受柏德輔導?」,願意的竟然是我這位「朋友」!自然地,我被問到是否願意接受,我竟像個蠢材,答說「是」。這學習環節結果成了個絕對的災難,組長只有將它腰斬。
課堂完結前,我們做檢討,輪到我發言了,我說:「看來今早有人給我預設了陷阱」。全組人都不作聲,忽然一位女士說:「不,柏德,是你自設陷阱」。她一作聲,我立刻知道她說對了;當我向我的「朋友」答說「是」那一刻的不祥預感,又活生生地浮現了。 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我作出了讓步 ── 唯一使我說「是」的原因是恐懼;我怕如果我說「不」,其他組員會怎樣看我。如果我誠實,我會這樣說:「不,我很不自在;我不感覺到自由。」可是恐懼控制了我。 然而,這是寶貴的一課;它教懂我恐懼不僅帶來沒有生命的交往,而且恐懼也會危及我們的誠信,我們同耶穌的關係,因為它損害我們的自由,削弱我們去愛的能力。 我們如何克服恐懼?我著實不知道我們能否做到,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恐懼可以是健康的反應。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他和五歲的女兒玩耍 ── 在客廳把她拋上半空,然後又張手接回她,小女兒玩得興高采烈。此時,她的四歲小弟弟進來,我的朋友便照著跟他玩。但當離開父親的手,兒子便驚慌大叫起來。我的朋友問兒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小男孩回答說:「我的頭差點撞到天花板!」「但你的姐姐並不害怕」,我的朋友說。男孩子嚴肅地說:「對,但她沒有思考」! 所以,在一些情況下,恐懼可以是適當的回應 ── 但至於恐懼成了是動機,那些不但不適當兼極具破壞性的情況又怎樣呢?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消除這種恐懼呢?我已經說過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恐懼例子,現在,我說些有關這方面的解救方法。 ── 第四章未完,待續 ──
© Copyright Shalom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