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怎樣利用《和平》祈禱? |
| 《和平》首頁 |
| 本月份《和平》目錄 |
| 訂閱《和平》 |
| 二零一七年八月《和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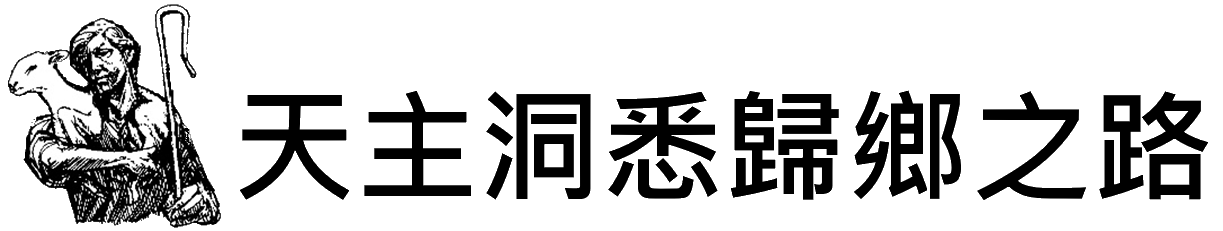 (譯自耶穌會士柏德•奧蘇利文神父 Fr Patrick O’Sullivan SJ 共七章的 God Knows How To Come Back) (續前) 附錄 天主子民與良心(續) 多年前,《神學研究/Theological Studies》期刊,載了一篇格拉澤(J. W. Glaser)的文章,當中列出超我和良心的分別。文章用了很多術語,我在這裏將其部分內容,以我的方式表述,冀能收幫助大家的效益。
神學研究,32(1971),38] 上面兩列,顯示良心的交往方式,基本上是以價值和關係為中心;超我的方式是恐懼,並以自我為中心 ── 無關係可言。這是兩者最大的分別。 但兩者也有些相似之處,因為兩者都關注什麼是「好」、什麼是「壞」。我們可以說,超我是我們的「初生良心」;而最理想的,就是這初生良心慢慢轉化,成為我們的真正良心。但是,如果這個轉變沒有發生,或只是某程度上部分發生,那麼,我們就注定對法律的理解,是個只顧條文字眼而非顧念其精神的守法主義者了。 這種情況發生在今天的教會嗎?教會的超我,蓋過了她的良心嗎?教會是否著重強調法律條文的字眼,而非法律所崇尚的價值?儘管不中聽,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因為恐懼是超我在運作的標誌之一。今天,教會最不需要,或天父最不願欲的,就是因畏懼權威而生的動機。這種恐懼鼓吹依照規定、法律等行事,而扼殺了內心的自由。 與此相反,在今天服侍教會的最好方法,就是培育和教養我們的良心 ── 「我們最秘密的核心和聖所……我們與天主獨處的地方」 ── 以便對教會的訓導保持開放和尊重的「友好態度」,分擔她所關注的,並推動那些能增強或保護我們在基督的奧體內建立起的關係質素。 這種本於對話與合作的前進方式,顯然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思想:
──── 全書完 ────
© Copyright Shalom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